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周纪鸿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年代。那时的董耀会既是秦皇岛的文学发烧友,更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热血青年。倏忽几十年过去了。他在27岁时放弃电厂的工作,徒步走长城,考察长城、叩问长城,进而研究长城。他匍匐在长城的身上,亲吻、追问,可以说将整个身家性命付与了长城。说白了,就是一辈子跟长城“拼”上了——先后出版了几十部、上千万字的有关长城的著述,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城研究专家。我打心眼儿里佩服赞赏他!借用奚学瑶老师的话说,他是“从秦皇岛走出的文化人”。

董耀会
其实,一个人一生最值得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深入的经历,再一件是充分的表达。如果说,董耀会和他的伙伴花508天徒步万里长城的风餐露宿是深入的经历的话,那么他之后所有的学习长城、研究长城、书写长城,全部精力献身于长城事业,开拓出长城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等所有派生出来的工作,就是充分的表达。这一切归根到底一句话,都体现了他不辍的攀登与不倦的追求!
一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嘉峪关关城考察时强调:“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磅礴力量。”
长城的历史,潜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基因和文化元素。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在于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博大精深。董耀会从1984年5月4日开始长城考察,也就从那天开始,他一步步走近了长城,也一步步走进了历史3深处。他用脚步丈量了长城之后,写作出版了《明长城考实》,随后又完成了通俗读物《长城万里行》、《瓦合集——长城研究文论》《守望长城——董耀会谈长城保护》《长城文化经济带建设研究》等系列专著,包括他参与筹建中国长城学会,担任国家“十二五”项目《中国长城志》的主编,从副秘书长、秘书长到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及至这部35万字的《长城:追问与共鸣》问世,充分证明董耀会先生40年来,一心投身长城研究的踏实足迹和显著成绩。

董耀会的《长城:追问与共鸣》这部著作结构上纵横交织,经纬清晰。纵向是指上自先秦诸侯国之间相互防御而诞生的大大小小城墙,延续至战国、秦朝,汉朝,北朝、隋唐、金代,重点突出明朝长城、直至清朝对明长城的再利用;横向是以长城的视角,长城的建筑、巩固、战火的焚烧、长城的损毁和修复、长城的军事指挥与防御系统、长城与国家治理、长城与王朝的经济关系、民族关系以及长城精神价值之洞见等。一方面研究长城在历史上的作用,从长城的生命视阈续写丰富中国的历史;另一方面在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命运共同体等维度洞察深蕴其中的奥秘,并进行哲学思考。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董耀会的《长城:追问与共鸣》具有田野考察的亲历性,这与以往常居书斋的历史学家们的鸿篇巨著不同,他的著述带着田野的芬芳气息,夹杂着千年的风霜沧桑而呈现在读者面前。以前的历史学家,大多是从史料考证到版本校勘,从史料中钩沉索隐,而董耀会的著述是从田野到典籍史料,再从典籍史料到实地考察,这就使他的文字既语出有据,又鲜活生动。历史地理学,只有真正进入田野,了解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才能领悟这个民族文化的真谛。徒步长城身体经验的族际共享,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长城所代表的民族历经磨难的多舛命运,而且思考了民族共舞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二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据资料统计,多年来围绕着长城出版的读物有数百种之多。但是,大多为旅游文化类、图片摄影类、古建筑资料类和历史文献类图书以及一些长城研究论文汇集等。这类书大多为满足一般读者、旅游者的需要,简单地了解长城的来龙去脉、建筑特征、风土人情、文史资料留存。老一代的长城学者、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的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的《长城史话》和秦皇岛市本土长城专家、原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郭述祖的《山海关长城志》以及曾任山海关区区长张立辉的《山海关长城》等书籍,为万里长城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发挥了基础性、奠基性作用。而董耀会的《长城:追问与共鸣》,无论从政治、军事和战争、社会、民族等主题的开掘、架构的创新、视域的扩大以及长城价值的识鉴等多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和突破,显示了新时代长城学者宏观的视野和不俗的学术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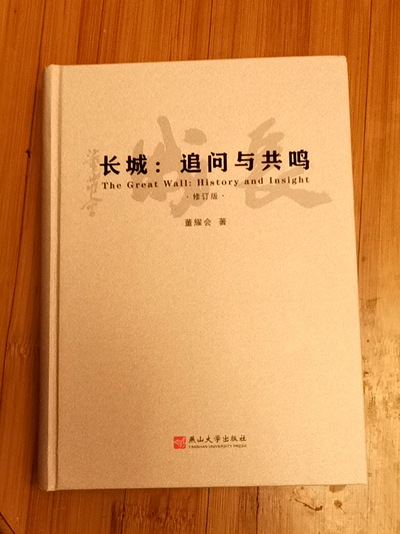
《长城:追问与共鸣》引述美国史塔夫利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谈到长城防御作用时的描述“游牧民族的入侵还常常是一系列爆炸反应的最终结果,攻不破中国长城,或者遇上障碍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往往使游牧民族转而西进。接二连三的入侵犹如不断向西的一连串冲击波,最终使游牧民涌过奥克劳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董耀会认为,匈奴人与蒙古人的西进,虽有着各自特殊的原因,但长城强大的防御使其不能轻易南下,转而西征也是一个原因。燕山大学出版社社长、本书出版人陈玉女士认为,本书对长城的认识,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人类社会的共识,冲破了长城奇观化的被观赏状态,凸显出长城文明价值的普遍互通属性。董耀会在书中追问的人类文明史上的三个基本问题,生死存亡、构建文明发展秩序、文明发展和延续。环顾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浪潮狂飙翻滚,俄乌战争炮火连天,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着核威胁的逼迫,日本的核废水已经泄入太平洋,使浩瀚的太平洋难以太平!阅读董耀会的这本书,时时令我耳畔响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历史悠久建筑宏伟的万里长城,不仅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物,凝聚着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也洋溢着一股执著求索的精神。
三
董耀会曾师从著名学部委员、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在严师的教诲下,他刻苦研读,围绕着长城的历史、地理、军事、建筑等多方面的学问不辍探索。《长城:追问与共鸣》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留下了他攀登的足迹和不倦的追求。除了著书立说外,董耀会的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宣传长城、研究长城、保护长城,恰似一个长城义务宣传员和长城社会活动家。除了曾受外交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给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等介绍万里长城之外,多年来,他活跃在长城的宣传、保护和研究等系列活动中。曾记得,他在北大学习研究时,曾组织编辑出版了《北大人》一书,使很多北大人的足迹和业绩令世人了解。他总是生龙活虎似的工作,新点子新创意迭出。这也使他总是敏锐地发现问题,走在长城学问研究的前列。

任何一门学科的创建都是不容易的,也是有远见卓识的人毕其一生所追求的。董耀会把眼光放在更根本也更重要领域——创建一门他所心仪的学科“长城学”。这本书,全景式展现长城历史脉络,皓首穷经,引经据典,庶几可以看作创建“长城学”的辅助教材。毋庸讳言,一门学问的形成以及一个学科的创建要经过多人多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实现。如果从筹建中国长城学会开始,那么创建“长城学”实际上已经走过了40年的漫长道路。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长城这个极具历史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图腾象征的伟大建筑,完全有可能成为一门显学。特别是万里长城的考古研究发现还在延续。据新华社西安2023年2月23日电,经过三年的考古挖掘,被黄沙掩埋了300多年的陕西清平堡遗址渐露真容。清平堡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镇东门沟村,为明代延绥镇长城三十六营堡之一,也是当时的互市场所之一。专家介绍,清平堡在修建之初既有军事功能也有商贸功能,营堡内留下大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遗迹,是长城两侧民族与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的见证。因此,一方面,考古发现为“长城学”的创立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也为研究长城提供了新的手段。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天津大学采用数字技术复原四种多媒体展示手段,带观众飞“阅”长城。
总之,长城是中华文化的研究涉及领域广、需要多学科的对话和互动,涵盖了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建筑学、民族学、旅游学、遗产学等多个学科交叉特点。非常可喜的是,燕山大学出版社以及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的专家团队和像董耀会先生这样的“长城之子”、专家学者们,继续发扬“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精神,共同在“长城学”的创建方面众人拾柴,添砖加瓦,“长城学”必将会走进教材,走进高校,与古老的历史地理和中国式现代化相衔接,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和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实践相吻合。我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董耀会创建“长城学”的夙愿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