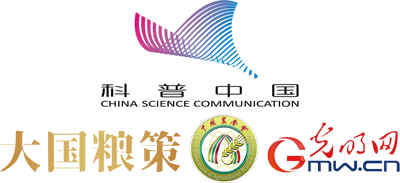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从远古先民采集野生大豆食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被驯化栽培,大豆历经演变,成为丰富餐桌的豆制品之源。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油料和蛋白质作物,其野生祖先(Glycine soja)约6000至9000年前在东亚被驯化为栽培大豆(Glycine max)。
然而,大豆是如何被驯化的?
大豆驯化的科学奥秘:人类如何改写植物的“生存法则”?
“多年生野生大豆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遗传多样性丰富,具有较强的抗逆、抗盐碱、抗虫、耐旱、耐热等特征,是栽培大豆进行性状改良的主要遗传资源。”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教授张大健说。
野生大豆(Glycine soja)原本是一种攀缘性杂草,种子仅有绿豆大小,成熟时豆荚会“爆裂”弹射种子,以确保后代扩散。但人类在驯化过程中,通过长期选择,逐渐改变了它的基因:
“不爆荚”基因:让豆荚成熟后仍保持闭合,方便采收。
“直立生长”基因:使植株从蔓生变为直立,适合密集种植。
“大籽粒”基因:让种子储存更多营养,成为理想的粮食来源。
这一过程被称为“生活史策略”的转变——野生植物为生存而“自私”扩散,而栽培作物则被人类驯化为“无私奉献”,把能量集中到人类需要的部位。
田间的野生大豆
现代科学的“逆向驯化”:找回丢失的耐盐基因
在驯化过程中,人类过度关注产量,导致许多抗逆基因(如耐盐、抗旱等)在栽培大豆(Glycine max)中丢失。山东农业大学大豆功能基因组学与遗传改良团队,利用泛基因组技术(超级基因库),构建了野生和栽培大豆高质量基因组及豆科超级泛基因组框架,发现大豆的基因像一块块“积木”:
(1)“产量区”(部分基因):控制籽粒大小、蛋白质含量等;
(2)“抗逆区”(另一部分基因):具有耐盐、抗旱等能力。
“长期以来,大豆增产幅度有限,绝大多数品种来自相同或相近的祖先。” 据张大健介绍,通过解析野生大豆的基因,可以为改良、选育新品种提供重要而丰富的遗传资源。张大健表示: “有了这些 ‘遗传密码’做基础,我们将目标锁定为“利用定制化分子育种,培育高产优质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像“拼积木”一样把抗盐,高产模块等装回现代栽培大豆,培育出“山豆”系列耐盐品种。
张大健在田间杂交
其中,“山豆2号”通过山东省审定,成为山东农业大学首个自主培育的大豆品种。这个能在盐碱地亩产400斤的品种,高产优质、抗逆性强,蛋白和油含量中等偏上,在省级实验中表现突出,为山东大豆育种提供了新的选择。
驯化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大豆的驯化史,是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缩影。过去,我们驯化大豆填饱肚子;今天,我们用科学“逆向驯化”,让作物适应更恶劣的环境。这不仅是一场基因革命,更是人类智慧对未来的投资——让盐碱地开花结果,让每一粒大豆承载更多可能。
作者:张金飞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
策划:林佳欣 武玥彤
科学审核:张大健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教授
支持单位:山东农业大学